《金瓶梅》不是,它的发展线索是一条线的。这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艺术上是有贡献的,有地位的。我说应该多注意这些地方,但是这些地方对一般读者是不是有意义呢?我也怀疑,你不研究文学,不研究古代小说,不研究《金瓶梅》,注意这些究竟有用没用?我也不知道。
材料三
主持人:我借刘先生的意思说,如果要是从中国古典文学伟大作品中汲取营养的话,青少年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最好多读《红楼梦》,少读或不读《金瓶梅》。[14]

材料一,刘世德先生的讲述与胡兰成对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认定并无二致,但在言语上更有着对《金瓶梅》强烈的贬斥成分。他认为《红楼梦》有生活的哲理性和诗的光辉,有使人向上励志的意义。
而《金瓶梅》基本是描写黑暗和腐朽的东西,且作者还带着欣赏去描写和展示这些不堪的内容。姑且不去究察《红楼梦》是否仅仅只是接受了《金瓶梅》的写作技法的影响,故能体现文本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说法是否合乎逻辑?仅就“看的人也是津津有味”一句,已经很能说明指向性阅读对于读者合目的性的重要。

刘世德先生
材料二,这是材料一中刘世德先生同一段主讲词的后半部分。如果说前半部分还能肯定一般读者可以用好奇,或者了解的心理来表明自己对《金瓶梅》的阅读指向性,那么在后半部分,刘世德却把一般读者的阅读指向性全部给否定了。也就是说,如果阅读指向“不研究文学,不研究古代小说,不研究《金瓶梅》”,那么阅读《金瓶梅》就只能有一个指向性:欣赏黑暗、腐朽的污秽。
如此一来,受众阅读指向性应该有限制性一说便随之得以成立,《金瓶梅》阅读应该受到禁止,也就顺理成章,合乎逻辑起来。研究者则因为阅读指向性的特殊需求,所以唯研究者才可读《金瓶梅》的逻辑,也就堂而皇之变成了唯一能容许阅读的原因。
材料三:傅光明先生的阐释正好说明本文对上述材料分析的准确性。傅光明不仅对阅读指向做出了一个设定:“如果……汲取营养”为目的,还对阅读者做出身份的界定,即“青少年大学生”,且强调“尤其是女大学生最好多读《红楼梦》,少读或不读《金瓶梅》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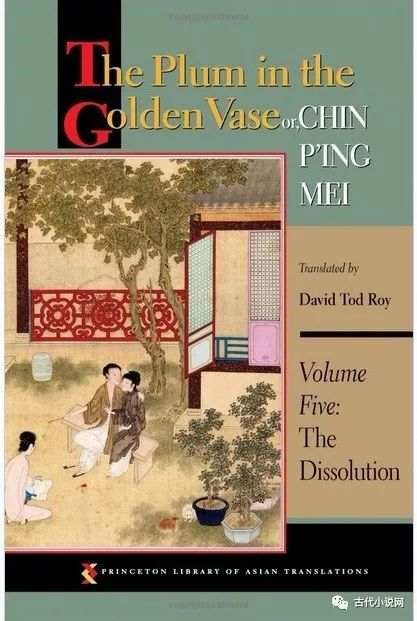
《金瓶梅》芮效卫英译本
而这份总结词出现有三个关键的信息:
一是说明阅读的指向是为得到“营养”,就是阅读文本是为了能喝上“心灵鸡汤”之类,这反映出一种对文学 “教化”功能传统的接受和积极提倡。
二是否定青少年可以因为好奇,而选择某种作品去进行阅读的行为合理性,强调阅读指向只应该与容许和导向保持一致。
尤其对于性别强调的说辞更是令人汗颜,其以关爱的方式对年轻女性阅读指向性告诫,话语中隐含的是十分明显的歧视态度。
之所以把一份共时性的材料分为三部分来做出分析,是因为材料对于阅读指向性的说明很具有典型性。阅读的指向性是阅读心理预期的初始,也是批评意识形成的一个基准。
人的阅读行为,如果不是无指向性阅读,那么在选择阅读对象时,便已经产生出对该作品的某种期许。这种期许有可能是有意识的,比如因为爱情有了“为你写诗的冲动”而选择阅读抒情诗;也有可能是无意识的,比如在一篇文章中所获得的美感熏陶。
3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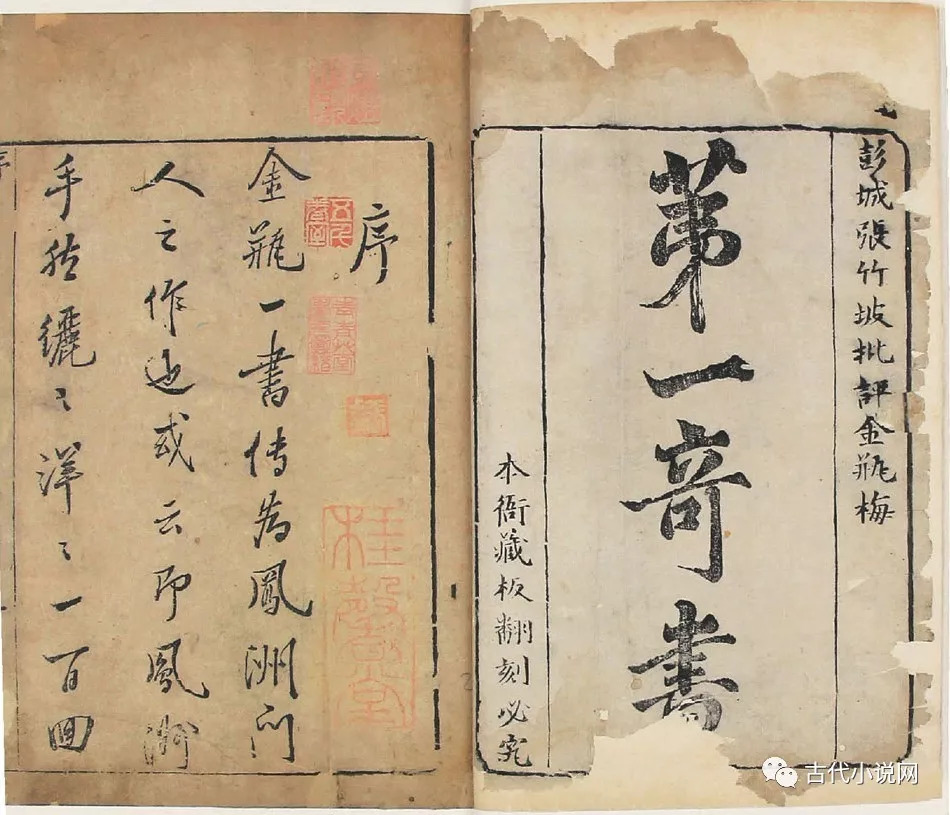
第一奇书本《金瓶梅》
对于《金瓶梅》这样的文学作品,属性的分类十分清晰,阅读的选择行为与阅读的预期也应该是相应的清晰。
台湾学者陈益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:“《金瓶梅》是一部淫书,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这是一本淫书中的淫书。父母、老师都规劝我们不要阅读。这是一部知名度很高的中国黄色小说之祖。”[15]
有不少资料可以说明,人们选择阅读《金瓶梅》的主要因由,便是“艳名”太甚的诱惑,这恐怕已无需举证了。既然就是冲着对感官的刺激和两性的性事描写而去阅读,《金瓶梅》却未能赢得类似于《如意君传》、《痴婆子传》那般的“纯艳情”,或可称为纯色情文学的头衔。
长期以来,关于《金瓶梅》是否应视为艳情,又或色情,再或者情色小说,以及它与中国艳情,或色情文学的关系等等,在学术界的争议就没有停歇过。且看以下材料以及分析:
材料一
我是鼓励人家读《金瓶梅》的,而且是理直气壮的读。我觉得《金瓶梅》是一部好书,且是一部极好的书。你说《金瓶梅》黄吗?是很黄,但黄得有理。[16]

《金瓶梅讲演录》
材料二
黄霖:这和日本的情况正相反:一方面是政府与一批文人一再强调要加以禁毁,决不予以宽容;另一方面却是不断地有人加以翻刻、评点,得到了一批文人的激赏。究其原因,我想主要的一点是,从《金瓶梅》问世起,中国的文人中自有一批人并不认为它就是一部“淫书”,而认为它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。 [17]
材料三
中华养生网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