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大多数人在创伤中逐渐安稳
1980年,我家搬到报社大院,原先住的纺织厂宿舍,留给了我姥姥。周五放学,我和弟弟便乘着厂车去我姥姥家。
厂区大门两侧的路牙子上,永远有吃晚饭的女工蹲成一排,白围裙,白色的软帽,帽檐下露出的头发上沾着棉絮。
她们一边扒拉饭盒,一边抬眼看着大巴,苍茫暮色中,她们没有表情的脸,如油画般麻木苦楚。
我和弟弟从厂车上下来,去我姥姥家。我们老是去我姥姥家度周末,不是亲情使然,探望之外的更重要目的是,我们要去洗澡。

那时候的冬天,没有取暖设施,在家里洗澡,是不可想象的事儿。
我妈也想过办法,在家中架起一个塑料薄膜做的浴罩,有点儿像蚊帐,澡盆置于其中,试图让热气挥发得慢一点。
但事实证明,这只是一厢情愿,热气流失的速度未必变慢不说,挥胳膊伸腿时,一不小心,那塑料薄膜就会贴到皮肤上来,数九寒天里,它的冰凉,比空气更有质感。
只能是去澡堂子。报社大院附近也有澡堂子,私人开的,面向社会,三教九流出没其间,像我爸妈这样的“公家人”,多少会有些嫌弃。
纺织厂的澡堂子相对单纯,也便宜,便成了不二选择,我妈下了早班或夜班后,会端着大盆,带着我来到澡堂子——我弟弟交给对门的叔叔照应。
纺织厂女工众多,女澡堂也宏伟,一长溜的淋浴头,雾气蒸腾中,站在这头,看不到那头。
我妈带着我,寻找空位子。这寻觅的过程,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打量那些女人。
她们大多是已婚女人,不少像我妈这样带着孩子——女工们通常结婚较早;她们身上大多有赘肉——
我妈说,如果不下劲儿吃,就跑不动,那赘肉,是劳作的身体下意识地启动了自我保护程序;不少人的身体上,还有一条蜈蚣般的深色竖形疤痕,剖腹产留下的疤痕。
很多年之后,我也经历了一场剖腹产,如今那疤痕渐渐淡去,渐渐看不清楚了,我依旧略感遗憾。
但在许多年前,我没有这样矫情,水雾里,那些带着赘肉、疤痕晃动的身体怡然自得,让我感到,疤痕已经与她们融为一体,与她们不完整的生活融为一体。
那些疤痕让我知晓,生活就是这样,在创伤中逐渐安稳,我们不可以,对它有太任性的要求。

希望变成她那样的女子
我再大一些时,就不大愿意去纺织厂洗澡了。我爸帮我发现了一个很近又很“规范”的去处:军分区澡堂子。
与我妈纺织厂里的澡堂相反,军分区的女澡堂很小,去了几次之后,有几张脸,看得熟悉起来。
有个高个子女孩,浓眉大眼,鼻梁挺直,又有一个小嘴和尖下巴,长得可谓标致。但我听到她在澡堂里公然谈论她的“个人问题”,说自己还没有对象。
有人用不能理解的口气恭维她的美貌,她说她也正为此烦恼,作为一个美女,她的单身使得她处处显得可疑。
她大着嗓门在一堆陌生女人中诉说她的烦恼,我当时就很容易理解她为什么嫁不掉了,她看得上的男人,只怕都很难爱上她“一览无余”的大嗓门吧。

相形之下,另一个经常出现的女人更耐人寻味。她的脸不算漂亮,单眼皮,眼睛也不大,却有一种简洁之美,衬得那个大嗓门美女的脸,都失之于用力过猛了。
她的身材也很简洁,看上去结实而富有弹性,像是经常锻炼的样子。
她身体上的神来之笔,是那挺拔的脖颈,许多次,我看到她仰起头,下巴与脖颈成一条优美的弧线,水柱重重地打在她脸上,水花晶莹,冲刷着她的短发,弹溅到她的肌肤上,我能够感觉到她的快意。
仿佛,是她的灵魂,在经受着这样一场强有力的冲击,我不由想,她一定是在爱着吧。
有一次,我们一前一后离开洗浴间,来到更衣的区域。
我看见她一件一件地穿衣服,那内衣,正如我想象中那样考究,她穿上了白色的棉毛衫,套上黑色的高领毛衣,跃进蓝色牛仔裤里,她的外套,是一件米色的风衣,她系好风衣腰带,将擦得半干的短发梳整齐,走出门去。
我跟在她后面。那时刚过完新年,地上是初融的积雪与鞭炮碎屑混合成的泥泞,我跟在她后面,心情复杂。
我并不是刻意要跟踪她,我正好也走那条路,可是,走在她身后,我的心思全在她身上。
那爱慕里,还有一种好奇,我想看看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样,我希望自己会变成她这样的女子,我一定要变成她这样的女子。
那时候我多大?16岁,还是18岁?我只记得在许多个年头里,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长大,想要一脚踏进更加精彩更加炫目的另外一种生活。
那种生活里充斥着各种元素,最主要的两种,就是美,和爱,不同寻常的美,和不同寻常的爱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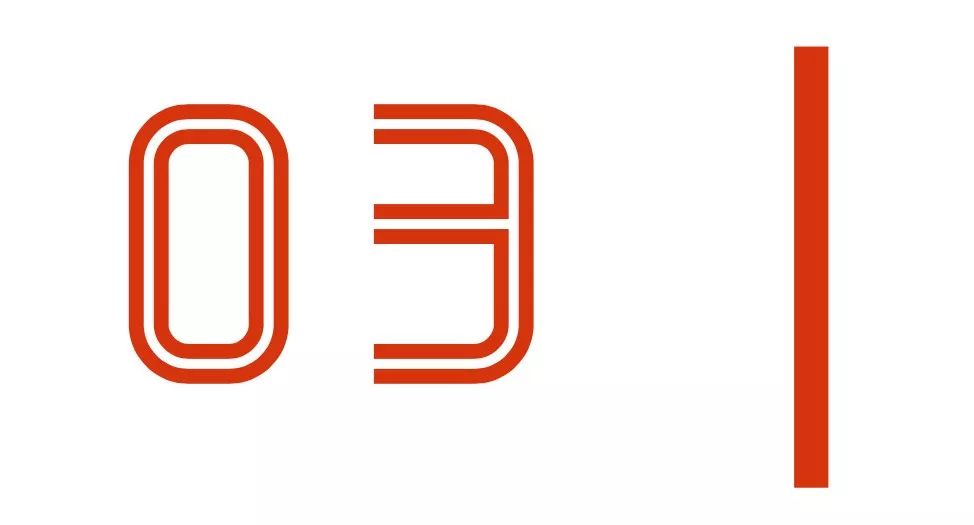
要做一个有故事的人
1994年,我离开家乡,去南方一所学校读书。宿舍后面就是女澡堂,出来进去的,多是住在那个校区的女生,绝少有生面孔。
有一天,我去得很晚,还有半个小时就关门了,我快刀斩乱麻般地洗了个澡,出来时,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在不紧不慢地穿衣服。
她已经穿好了棉毛衫,正在往棉毛衫上套假领子,如今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们一定不能明白假领子这种东西。
它是一件衬衫的局部,只到胸口,没有袖子,从外套的领口看,它貌似一件完整的衬衫,脱掉外套,才会发现它。
袖子,从外套的领口看,它貌似一件完整的衬衫,脱掉外套,才会发现它是那么滑稽。
但在当年,假领子还算是时尚人士的爱物,意味着对于生活品位的顽强追求,它出现在这个老太太身上,简直让我肃然起敬了,高龄如她,实在不必将自己武装到领口啊。

我一出神就有点儿失礼,她也注意到了,竟然,朝呆望着她的我眨了眨眼。
近乎顽皮的一眨眼,也将我惊住,赶紧收回目光,却用余光瞟到,她拿出一把精致的小梳子,一下一下,梳她花白的头,随着手势,她的指间有什么一再闪耀,看仔细了,却是一枚钻戒。
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,钻戒尚未飞到寻常女人手上,而这个老太太,她有70多岁了吧?却稀松平常地就拥有一枚。
我觉得不能再将她等闲视之,那么,她和她的钻戒,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这个女生宿舍后面的澡堂子里呢?我发达的想象力,马上给她设计出一套前尘往事,我想,她一定是来缅怀的。
她可能曾是这个学校里的一个女生,月白衫子黑短裙,黑发齐耳,步履轻捷,她可能在这里爱上过什么人,然后失散,她的人生又经历了许多事,有了丈夫和一堆儿女。
但当她进入垂暮之年,越来越想回到这里,不只因为这是曾遇到过他的地方,还因为,她想在这里,与记忆里的那个风华正茂的自己相遇。
这样想着,我又认真地看了她几眼,我知道,我看的不是她,是我心中那个,未来的自己。
然后,我们几乎是一起,掀开那个软塑料的门帘,走出澡堂去。
作者:闫红,来源:《品读》2018年第3期,摘自《彼年此时》一书,中国华侨出版社
主编:孙爱东 |版式:张初 |编辑:张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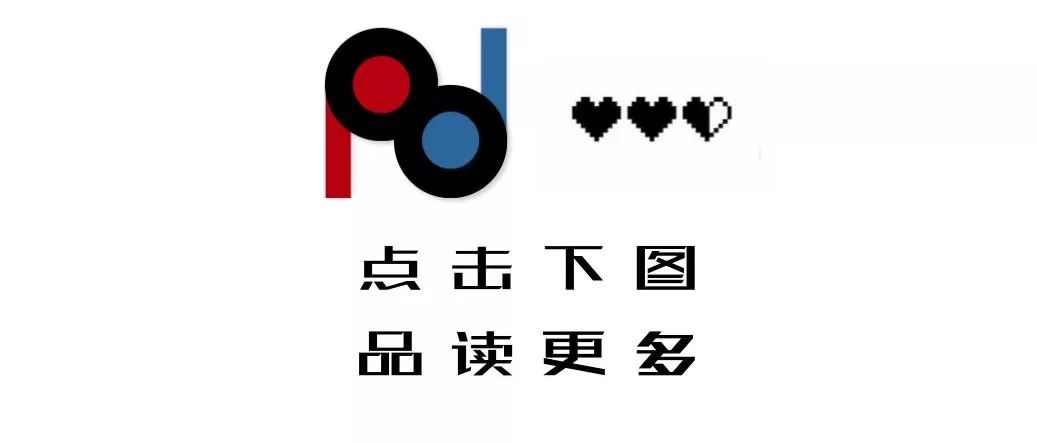





中华养生网

